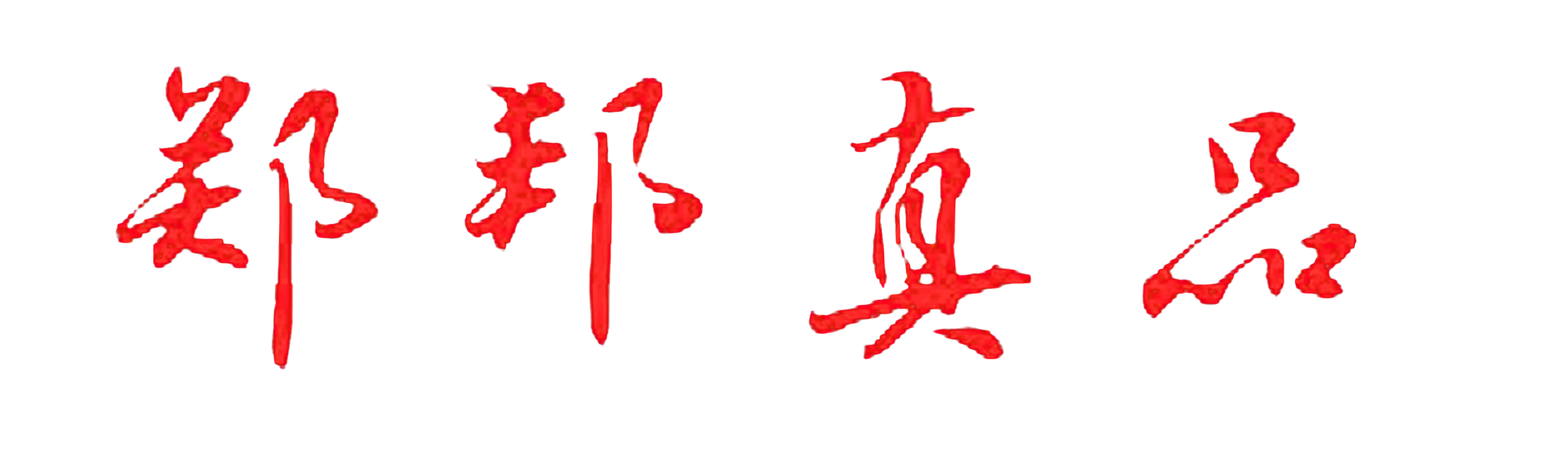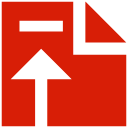电脑音响悄无声息地不见了,几天的沉静却拨动了我的琴弦,想倾诉点什么呢?那就把岳母的故事唱给你听。
岳母家和我同村,我小时候就对她有深刻的印象:走得快,会干地里的活,整天微笑着,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。
我和四梅的婚事是在大姨的撺掇下,岳母做主定下的娃娃亲。
关于岳母的故事大多是在和四梅的日常说话中知道的,一部分是从大姨和村里人哪里听到的。
岳母这个称呼在我口里叫着别扭,还是习惯叫她母亲好。
一
母亲的娘家坐落在涧河东岸的小山坳里,村名叫阳坡洼,只有几户人家,满山遍野的洋槐树把小村庄围得安安静静。
听大姨说母亲比她小11岁,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。那时候涧河对面的大青山上住着一群日本人,山脚下的村庄经常会受到日本鬼子的侵扰。阳坡洼同样也躲不过日本人的铁蹄,大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好和鬼子周旋的准备。
当鬼子们走到涧河西岸时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是在长辈的带领下,不声不响地迅速向东面山顶的树林里转移。等到村里没有了声响,乡邻们都确定日本鬼子走远了,然后再回到村里正常生活。
大姨还给我说过,躲日本人哩时候,一般都是她负责背着母亲往山上跑。
可是有一次不知是啥原因,大姨和村里人都准备跑哩时候,就是找不到母亲了。在院门外刚找一小会儿,就听到日本人的喊杀声了,大姨一时头蒙没有了办法,只好跟着人群往东山顶跑去。奶奶、舅舅知道母亲被落下了以后也没有责备她,都是憋着眼泪注视着村庄,那时一家人的痛苦心情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,村里其他人也都是焦急万分。
村庄安静后,大姨急切地跑回院子里,看见母亲一个人平静地坐在门槛上,全家人七上八下的心才平稳下来。过了好半天,大姨平和地问过母亲后才知道:村里人都开始跑哩那会儿,是她一时疏忽没看见柴火垛茅厕里的母亲。
当母亲蹲坑出来后村里都不见人影了,刚坐到炕台上就听见房后有日本人叽里呱啦哩在大声叫喊,没过一会儿,日本鬼子咔嚓咔嚓的皮鞋声就来到了院子里。当刺刀哐啷一下把堂屋门撞开后,她都看见那日本人瞪着眼端着枪站在堂屋门口,自己也不知道害怕,依然坐在炕台上一动不动,那鬼子看着母亲,母亲就用镇定的目光回应着那日本人。
日本人狐疑地把露着顶棚的空屋子扫视了一遍,突然慢慢哩放下手中的枪,走过来把母亲抱了起来,嘴里轻声地说了几句听不懂的日本话,然后就把母亲又放在了炕台上,轻轻地关上门,扑腾扑腾地走出了院子。
也许是母亲那清澈明亮的眼睛里透射出与生俱来的纯朴与善良,打消了日本鬼子内心的邪恶,让她逃过了一劫。
母亲的幼年是在战乱年代的喊杀声中度过了。
二
我和四梅只要一回老家,在路上总是要把母亲的故事说个够,母亲的好多生活细节都是从四梅口中得知的。
四梅告诉我,母亲到了即将出嫁的年龄时,正逢阳坡洼的刘家和东山顶的韩家连续多年争林地,人声鼎沸、骡马嘶鸣的场面常常发生,母亲顶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父亲走到了一起。
母亲初到韩家的第二天,看到的场景是爷爷怀里抱着四叔,边上还站着三岁的姑姑、五岁的三叔、八岁的二叔,不大不小一群小娃娃,你哭他闹磨人要吃哩。但她没有退缩,一声不吭,开始烧锅做饭干家务,屋里地里全把行,每天都把姊妹四个照顾得高高兴兴哩,让家里不再有小孩的吵闹声。
用母亲的话说:“看着愁也不行,得先弄点饭叫吃吃再说,把嘴一糊住,都不恁心焦人了。”
当爷爷这幼儿园园长退休后,母亲就成了大管家,姊妹四个相继成人,立起了自己的门户,父亲母亲两个人默默的就完成了一项大任务。
幼儿园再招新生,就有了姊妹七个相继入园的童年快乐。
每天早上起来母亲都是先把饭做好,再扫院子干家务,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,也不大声喊叫孩子们起床。等到姊妹几个睡到自然醒,再招呼着一个个吃饭,有人不想吃了,母亲就给谁再做,有时候一顿饭能做好几样。姊妹几个受母亲的感染,吃饭不吵不闹,说话轻声慢语,吃饱了都自己出去玩了。
四梅常给我说,母亲可好干活,叫干点活她可高兴,你不叫她干活她都不愿意了,你看她咋说哩:“坐那儿歇着是一天,干着活也是过一天,干点儿活怕啥了,那累不着。”
母亲人到中年时,上有老下有小,干了这活下来干那活,一天到晚都不停歇。
全家十几口人的一日三餐都是母亲一个人做的,每顿饭她都能提前准备好,听着家里人的脚步声来盛不同的饭菜,并准确地放在每个人的座位上。母亲的茶饭做的不但好吃还样数多,她做的锅底拱是村里一绝,要是谁家来重要客人了都会喊她去帮厨。滋滋啦啦、铿里哐呛、咣咣铛铛声是母亲每天反复演奏的厨房进行曲。
她做针线活也是一把好手,村里的屋里人成天会来讨要鞋样,请教剪衣服的尺寸。她也从来没耽误过供姊妹六七个穿鞋穿衣服,每当到快换季时,姊妹几个都是经常听着母亲刺啦刺啦的纳鞋底声,哒哒哒的缝纫机声进入梦乡。
像犁地耙地、碾场扬麦、聚麦秸垛这些男劳力干的庄稼活她也都会干,夜晚还会挽起裤腿站在田埂上听水声辨别田地里水浇的程度如何,当水声呼啦呼啦响时,都知道不是地边透水洞就是地里水溢出堤堰了。
母亲她从来都不叫苦喊累,天底下的苦对她来说好像都不叫苦,每天都是微笑着面对她眼中的活,只是静静的享受着生活的交响乐。
三
耳听为虚眼见为实。
我到十六七岁的时候,第一次到母亲家里帮忙干点活,早上一不小心睡过头了,起来后刚走到堂屋前檐下,母亲就微笑着把洗脸水端给我:
“早着哩,多睡一会儿,今天没啥活。”
当我看见锅屋地下水桶里的水满满的,心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叫我先把水倒缸里,再去挑一担。”
母亲温和地说:“先吃饭,吃好饭再说。”
可我走到锅屋一看,水缸里也是满满的,锅台边的柴火一大堆。
我有点纳闷了,咋没听见一点响声呢?四梅给我解释说,母亲她从来都不喊叫她们姊妹几个去家务活,每天早上,她总是先把水担回来放在哪儿,等到孩子们都起来后再往水缸里倒,轻手轻脚地切菜、拿碗筷,蒸馍的时候锅底不放碗底个个儿,扫院子时也是轻轻的,柴火都是在白天抽空准备好。
她更不指望她们姊妹几个去干地里活,习惯习惯一个人去干屋里屋外的农家活,当她们意识到的时候,她总是笑呵呵的收工了,还赶着她们回家多歇一会好上学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来回走动的次数多了,我也悄悄地融进了母亲家里的生活。
到了大哥结婚后的那段时间,两个弟弟正好在外地求学,家里经济有点吃紧,父亲七凑八借开回来一辆二手南京卡斯车,到南沟山上拉矿石支撑家庭开支。
母亲虽没有跟着上山,但她会在家里一边干活,一边操心着掌握对面山上父亲车的行踪。父亲的车一开始过南沟崖豁时,母亲都能第一时间听见,然后赶紧放下手中的活,给我们交代一下就回去了,边做饭边听着车声计算着时间。当父亲的车停靠在上河石料厂,车厢板哐当一声打开时,母亲就开始下面条,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家门口时,她就把父亲最爱吃的面条刚好放在门楼下的方桌上,从没耽搁一点儿事。
时间长了,母亲练就一种能辨别父亲车声音的本领。
我时常抱着好奇心向母亲请教,她就耐心地教我们听父亲车的声音。停车时的哼哼声有顿挫,轻声匀速稍快的哼哼声是车开始走到杨树行了,几声大油门紧凑的哼哼声是在上河滩小坡,开始长时匀速费劲的哼哼时,是开始爬南头沟陡坡了,到车翻过山梁声音再次匀速放慢时,母亲就开始放心地干活了。重车回来时,母亲主要是依据刹车声响亮不响亮、刺耳不刺耳来判断父亲的车在下那个坡拐那个弯,走平地时车声哼得比较低沉,也会有快慢变化。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出来,听了母亲的描述以后,仔细听了一段时间就能辨别清楚了,父亲的车声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
我和四梅结婚后,父母亲的好多事我都亲身经历过。
老二兄弟结婚后,买了一辆摩托车,母亲也能听出来和其他人的摩托车声音不一样。一次母亲、四梅和我在院里剥玉米,母亲突然说:“我得去做饭哩,永军从段村学回来拿东西了。”
四梅说:“没有打电话,也不见人影你先坐着歇一会儿,真是回来了再去做也不迟。”
母亲说:“我听见永军的摩托车声到上疙瘩了,他还有课哩,叫你看见到屋都迟啦。”
十分钟后,二弟真的骑着摩托车噔噔噔地回来了,我心里一颤,四梅却说:“这就是妈的本事。”
后来姊妹几个都有车了,唠家常时母亲也会给我们分享谁家的汽车声音有特点。
四
老三兄弟家娃的满月鞭炮声响过没两年,从没说过这疼那疼也从没吃过药的母亲,双腿和手腕出问题了,有时候疼得整晚都睡不成觉。
从郑州看病回来后的一段时间里,咕嘟咕嘟的中草药开始满屋飘香,大把大把的白色西药片还得继续吃,母亲慢慢的开始整天打嗝儿,比普通人打嗝儿的声音要大,那时候都没在意,母亲还整天开玩笑说:“才不干活了,吃吃饭消化不好啦。”
有好几次半夜醒来,都能听到母亲和父亲还在说话,后来就问母亲:“你俩晚上不睡觉,说啥话哩?”
母亲就会给我们透露了一点儿她的止疼秘诀:“晚上疼哩没办法,就和你爹一块挨个说说孩子们的事,多想想娃们哩好事都不疼了;白天疼了就干点儿活来排解,真疼哩厉害了,都叫它疼,你不想它都算了。”
病魔缠身的母亲从来都不舍得停下她手中的活,干着干着手腕僵硬了,腿腕弯曲也伸不直了,走起路来已不太灵变,先是拄着一个拐杖,再下来驾双拐,再后来就坐在吱扭吱扭的轮椅上度过了人生的后半段。
连续几年里的每个月底,母亲都要到义马局医院做血沉检查,基本上都是早上来下午回山后,一年冬天准备回老家的时候下雪了,母亲就带着轮椅在我家里小住了几天。
嘴里整天说着:“看你们都忙成啥啦,我这老闲人成天来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我微笑着说:“说那是啥,这不是天不好嘛,平时叫您来您也不来,看这儿多暖和,不回了搁这儿过冬,到过了年再回。”
母亲说:“你爹在家吃不成饭,天一晴都得赶紧回去哩,你们该去干啥了都放心去吧,出去了给我放点戏听听都中了。”
于是第二天出门的时候,我就把电脑放到客厅里的电视柜上,打开爱奇艺播放戏曲片,并给她交代好,要是电脑黑屏了,动一下鼠标就开始唱了。
中午回来的时候,看见母亲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说:“《穆桂英挂帅》都快看完了,机器不唱了,按你们交代的我用拐棍儿一捣那塑料疙瘩,都又开始唱了,怪好哩。”
从那以后,母亲每次来我家时,就用电脑放些她喜欢的豫剧选段,全家人一块来听那板胡配上锣鼓家伙伴奏的河南戏曲。
五
2017年元旦前,大雪封山,回山里的路滑不通车。
父亲来电话说母亲两星期来的病情加重。
见面后,母亲还不停地叨叨父亲好麻烦人。
母亲住在医院里的第9天晚上11点多,大哥哆哆嗦嗦的电话声把姊妹几个都喊叫到病房里,看到母亲正昏迷说胡话。
把围巾解下来,说是大姐买给她哩;把床头的衣服叠好再摊开,说这衣服可贵,是三姐从西安带回来的;不停地拽着毛衣说这可暖和,是大孙女从上海带回来的;一会儿叫二弟拿这东西,一会儿要三弟搬那纸箱;一会要出去看看家里的鸡狗喂啥东西没,一会儿呼唤二姐:“把案板上的扁食收拾好,看猫娃拉走了。”
……
清醒后一看见全家人都守在医院里,就开始嚷嚷了:
“你姊妹几个都能过,我走了也可放心,七十多哩人啦,都够中了,啥都有了还想咋哩?你们都赶紧回去吧,赶紧都回吧!留一人都行了。”
再次昏迷,第二天清醒后对我们说:“你看我这孙娃、孙女都长哩可好,上学也不赖,咱家有真些人,我可满足。”笑着说着把枕头下边父亲过生日时拍的全家福拿出来叫我们大家看。
母亲第三天晚上在昏迷中醒来,当着我们几个的面看着父亲说:“其他都没啥放不下哩了,就是担心你爹不听话好爬高上低,年龄大了干啥都得小心点儿,能干了干点不能干了都算了,别给娃们扒窟窿。”
那几天清醒时说话的语气、声音和正常人一模一样,晚上睡觉时还和平时一样打呼噜。
到腊月23 那天,母亲被送进了ICU。二弟传过来的视频里,看见母亲艰难地做着手势,用微弱的声音说:“我好好着哩,不用担心,你们有事了都去忙吧,我停两天都回去了。”
她的目光依然让人羡慕不已,嘴角的微笑却被面罩上的水蒸气遮住了半边。
腊月25上午,第四次接到母亲的病危通知书,主治大夫反复和我们通报着母亲的呼吸情况,“已尽力了”一句话让医护办的空气瞬间凝滞,姊妹几个开始泪崩。稍微平静后,父亲和我大哥大姐们商量着面对现实,最后决定让母亲回老家再看看自己亲手盖的楼房。
六
车还没停稳,院子里炊烟缭绕、人来人往的画面,已模糊了贴着太阳膜的车窗玻璃。等候已久的街坊领居看见我们回来,一下子就围满了大门口的空地,俨然一种农村过大事的气氛。
母亲下救护车的刹那间,呼嗒呼嗒的塑料呼吸器声划破了寂静的小山村,在十多米开外的地方都能听见,盖着棉被的胸口一起一伏也能在远处看得到,此时的母亲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吸家门口麦田里熟悉的空气。
母亲一动不动躺在自己的床上,急促的喘气声一声接一声,屋里的所有人都在背后不停地抹眼泪,间歇性地能看到母亲眼中会有泪水溢出,但口中已说不出话来。
天黑的时候,村里别人家母亲都在收拾豆腐渣,我们的母亲却悄悄地跟随着玉皇大帝远行了。
一个既近又远的地方就在老家的北山上,那个既远又近的地方也在阳坡洼的东山上。洋槐树林里没有一丝风声,也没有一丁点声响。
母亲静静地躺在那温暖的山坳里。
母亲,转眼间您已走了近三年,但一直能感觉到您还在我们身边。
就是不知道天国里有没有病痛?有没有轮椅?也不知道您那里有没有音响?能不能播放父亲的汽车马达声?能不能下载您喜欢的两根弦的板胡声?
没有回响也可以。当您想我们的时候,那鞭炮声响就是我们对您的思念。
作者:王小伟 渑池县第二高级中学

1760元就能成“特级非遗传承师”:哪来的胆量,敢以文化部之名贩卖身份证书?
一批行业协会商会清理“特邀副会长”“名誉理事”等头衔
公司15人,13名女员工集中生育?“生育津贴”何以成了不法分子薅取的“金羊毛”
供货705万,给医生回扣247万!
收1500元请人打扫教室,莫让家长委员会也成背锅侠
监管“利剑”出鞘,整治市场竞争乱象
金晨涉嫌交通肇事“顶包”?事过十个多月后才公开爆料,其动机究竟是什么?
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八起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
急难事项“小额快救”办理不超3天:能否出台更多优惠政策,惠及更多群体
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第五批直播电商领域典型案例
公园内的母婴室紧锁:原本要便民服务的设施,为何偏偏成摆设?
重庆璧山“一火锅店向消费者收辛苦费”
用“假人”冒充押运员:造假何以不断?让造假成过街老鼠真的很难?
2025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余起
转眼已三年!怎么能忘却内心深处的痛,与记忆
用“假人”冒充押运员
拟清退300名超期学生:板子岂能只打在学生身上
凌晨点外卖致银行卡被风控?
线上打擦边引流,线下卖课:绝不能让挂羊头卖狗肉者再成“网红”
涉抄袭剽窃、论文买卖,一批科研不端行为和项目资金违规案件被通报